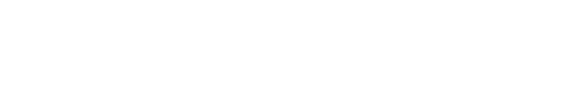每当我路过西安小寨,目光总会被兴善寺东路上那一片葱茏所牵引。时光的潮水退去,那扇熟悉的校门早已隐入城市更迭的皱褶,但记忆深处,“陕西教育学院”六个字,却如同当年校门前那株虬枝盘曲的石榴树——年年五月,灼灼其华,映照着几代人负笈而来的青春。
1991年秋,背负行囊的我站在兴善寺东街69号的校门前,仰望着那六个斑驳大字。作为政教系91级1班的新生,我带着关中县区三年教龄的困惑与渴望,一头扎进了这座“三秦教师的摇篮”。校门内那株虬枝盘曲的石榴树,从此成为青春坐标——五月花开似火,恰似我们这些在职学员眼底未熄的教育理想。

这里,是无数基层教师生命的中转驿站。校史馆里泛黄的纸页无声诉说:从1906年西安师范学校的草创初啼,到1978年陕西教育学院正式定名,再至2012年改制为陕西学前师范学院,百年风雨兼程,两甲子筚路蓝缕。校门内外,身份各异却怀揣共同热望的灵魂在此相逢——风尘仆仆从陕北高原走下的乡村教师,关中平原课桌后心怀不甘的年轻面庞……“成人教育学院”的身份,曾如一枚隐形的印章,烙着我们一丝难以言喻的复杂心绪。然而正是这“在职进修”的底色,让每一滴时光都浸透着更深沉的渴望。我们背负着讲台下无数双期待的眼睛,也背负着自己不甘沉寂的灵魂,步履匆匆地汇入这方不大的天地。
走进教室,便踏入一片人格与学识交织的星河。哲学课堂上,清癯的张老师指间常夹一支烟,烟灰在慷慨激昂处簌簌而落,仿佛思想的余烬灼烫着空气。他纵横捭阖,艰深的哲理竟如溪流般清澈流淌。班主任郭秀芬老师温润如古玉,她轻轻一点拨,常使蒙尘的才思骤然绽放光华。那双清澈的眼里,盛着对每个学员的深切关怀。忘不了那位山城来的同学深夜高烧,她在家中煮好一小锅鸡蛋面,热腾腾端到宿舍的情景——那碗朴素的面,足以温暖异乡人半生的记忆。
政教系的课堂是理性与激情交锋的战场。讲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》的吴特立老师,常将政协委员的调研案例化为鲜活教材。一次剖析农村教育失衡,他拍案疾呼:“教育公平不是口号,是千万个教室里的灯火!”——这句话如楔子,深深钉入我执教的初心。而在隔壁中文系的旁听课上,李志获先生正擎着烟卷侃侃而谈《离骚》。清癯的身影倚着讲台,先秦的悲怆在他沙哑的诵读中劈开时空:“屈子叩问的不是苍天,是知识分子的脊梁!”烟雾缭绕间,文学与政治的光芒交相辉映,照亮了我们这批“大龄学生”的精神荒原。书法课的李老师则以墨香重塑职业尊严,她铺开宣纸示范“教”字的魏碑体:“左边是‘孝’——对文化的敬畏;右边是‘攵’——鞭策之力。无敬无以立师,无韧无以育人。”
无数个夜晚,昏黄的灯光下,摊开的课本与教案沙沙作响。我们这群“大龄学生”,怀揣着对知识的敬畏,笨拙而固执地追赶流逝的岁月。书包里校门外的肉夹馍是深夜苦读的慰藉;老师悄悄塞来的牛皮纸包裹的油条,是清寒日子里沉甸甸的暖意。成人世界的窘迫与学堂的纯粹在此奇妙交融。校园虽小,却足以安放我们迟到的青春与不熄的梦想。周末偶尔的登临——华山的险峻,翠华山的幽深,大雁塔的沉静,兴庆公园的一池春水——都成了繁重课业缝隙里透气的窗口,生命版图上难以磨灭的坐标。

九十年代的校园,激荡着思想解放的洪流。我们在苏联援建的灰砖主楼里,见证着时代的嬗变:
课堂外:周末挤进电教室看“南方谈话”直播,同学们为“市场经济姓社姓资”争得面红耳赤,笔记本上落满激辩的墨点。班长毛警在学院的演讲大赛中屡屡夺魁,我的同学李光泽、武文海主编的《琴弦上的太阳》——大学生诗文集萃在西安南郊高校中熠熠生辉。实践中:随院团委赴周至县乡村中学实习,目睹民办教师王老师就着煤油灯批改作业的剪影,那一刻,吴老师“教育是暗夜星火”的箴言才真正刺透心灵。
毕业季:手握改制的《陕西教育学院学报》毕业专刊,头版标题如预言般闪烁——《师范转型:从知识搬运到生命点亮》。
后来,校牌终究换作了“陕西学前师范学院”,那栋主楼也成了教授们的生活区。岁月流转,我们如蒲公英散落四方:李光泽,从绥德、吴堡、清涧走来,如今在榆林市委党校担纲重任,他的诗歌散文在《人民日报》《光明日报》《陕西作家》上绽放光彩。同桌宋荣彬,转行神木市委党校,勤学不辍考取律师资格,成为当地名律。总“逃课”写诗的武文海,毕业后投身公安,扎根略阳县基层所长岗位。他创立此在主义诗歌流派,发起“新口语思潮”,身兼全国公安文联诗歌分会理事、陕西省青年文学协会副会长,诗集《我,在此》《翠峰纪事》相继出版,诗作译作频现重要刊物。我的散文集《站在秋天的阡陌上》出版时,他倾情推介,情谊如初。而我,虽已离开讲台多年,先后在扶风县城关街道、县食药局、住建局、农业局任站长等职。但那些早年发表在《陕西教育》上的论文,字里行间依然跳动着母校赋予的脉搏。
2012年,闻知母校更名,心头百感交集。默念贺词中“关中书院明脉薪传四百载”,蓦然哽咽——眼前浮现政教系教室墙上冯从吾的名言:“以心印心,如灯传灯”。无论身居何位,陕西教育学院的印记,早已融入血脉:那是“厚德博学”的箴言刻骨,“知行统一”的烙印铭心,更是“学高身正”的永恒标杆。
校门前那株石榴树,想必依然年年结籽,籽粒晶莹,饱含岁月的酸涩与回甘。它默默见证着一代代如我们这般背负行囊的过客:来时怀揣结茧的教案,去时肩披思想的锋芒。在这精神的驿站汲取火种,再散作满天星火,燎原于三秦大地最偏远的角落。教育的真谛,何尝不是如此?它未必总是殿堂金顶的光芒万丈,更多时候,是荒原上不期而遇的薪火相传,是暗夜里悄然递出的一豆烛光。
曾经以为离开的是校门,后来才知,走出的是我们——而那座以“教育”为名的精神圣殿,早已以知识为基,以师道为梁,以无数平凡灵魂的微光为瓦,永远构筑在灵魂深处最明亮的地方。它时刻提醒着我们:无论走出多远,总有一处精神的故园,如石榴花般灼灼不灭,映照着最初出发时,那份朴素而庄严的信仰——两载淬火,半生燃灯,此谓陕教院人的“知行统一”。
作者:杨云冰,毕业于陕西教育学院政教系91级1班